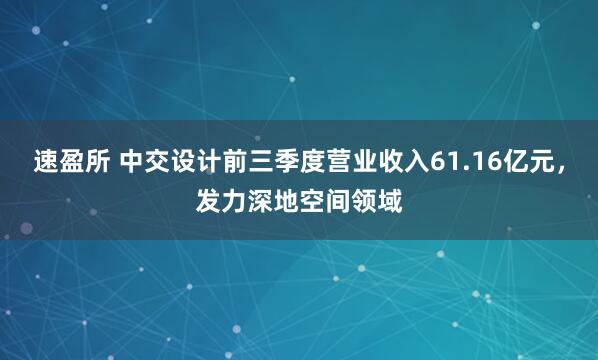1967年10月17日深夜,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昏黄,夜班护士把体温表收进搪瓷托盘红牛策略,一抬头发现23号病房的指示灯熄了。两分钟后,值班医生确认:爱新觉罗·溥仪,脉搏停止,终年61岁。消息还没传出院门,院内行政科已经为一张死亡证明的职务栏犯了难——写“皇帝”不合时宜,写“公民”又怕惹口舌。
院方次日递交的暂定文本是“协和医院特聘文史资料员”,公文一路送至东交民巷,却在国务院办公厅被退回。文件夹上夹着一张便笺:“身份务必准确”。一时间,谁来定调成了首都小范围内的公共话题。街道革委会的代表直接拍板:“普通居民就行。”而溥仪的胞弟溥杰说得委婉:“再普通,他毕竟是宣统。”

20日凌晨一点,西花厅灯还亮着。秘书轻声禀报:“总理,东城那边拿不定主意,家属请求指示。”周恩来放下钢笔,略停半秒,只一句:“照他们祖宗的规矩办,但勿铺张。”短短十四字,很快让所有争执熄火。
指令传到东冠英胡同时红牛策略,正对着骨灰盒发呆。三天前,她还在菜摊为一毛三分钱的白菜帮子与人讲价,如今所有目光一下聚到她身上。旁人私下咕哝:“末代皇帝,可不能让旌旗招展地走最后一程。”她红着眼眶也不出声,只把那行字默念几遍:“勿铺张”。
棺材问题紧接着浮上台面。族里耿直的长辈坚持金丝楠木,理由是“祖制不可失”。街道革委会一听火气蹿上来:“讲祖制?那还革什么命!”派出所抽调干警维持秩序,身材瘦高的所长张连魁——当年辽沈战役的排长——叼着半截烟,朝双方摆手:“事已请示中央,谁也别逞能。”
22日,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人员与溥杰一同前往八宝山选址。墓区管理员低声提醒:“此处埋的多是抗战、解放时期的烈士。”可周恩来给的批示里有“以团结为重”五字,谁也不敢擅自改变。转到东北隅,一块背阴地最终确定。溥杰蹲下,抓一把湿土,望着松根喃喃:“比起景山,这里倒也静。”

葬礼被定在23日上午十点。雨丝密如牛毛,合计不到三十人到场——亲属、邻里、民政局代表,再加两名在管战犯改造所时的管教。没有礼炮,没有挽幛。一对青年工人抬着方形骨灰盒走向墓穴红牛策略,步子却意外一致。管教轻声说:“稳点,别磕着。”工人只点头,并未回复。
值得一提的是,骨灰盒正面刻着“公民爱新觉罗·溥仪”十二字,背面则是“生光绪三十二年,殁一九六七年”,字体由文化部书法家即兴题写。刻工是京郊普通石匠,用时三小时。石匠纳闷:“按说宣统帝,用不了这速度。”可干部只说一句:“哀荣不在雕琢。”
下葬后第三天,文物出版社年轻编辑拿到《我的前半生》手稿修订稿。书页右上角保留着周恩来曾用的红蓝铅笔划痕,编辑惊奇:第246页那句“我三度登基,却始终是傀儡”旁边标了重重折线,还加批“可作警示”。那一年,图书未能如期付梓,却在干部读书班内部影印,以供学习。
有关“金銮殿余晖”的小道说法仍在胡同间流窜。有旗人后裔半夜抱着二锅头揶揄:“祖宗走了,京官该摘冠缨。”巡夜民兵犯难,抓吧?而上级明令:不扩大。溥仪曾在植物园做园丁,搭伙的老金头得知噩耗,只嘟囔一声:“老爱吃甜豆腐脑的人,还是撒手了。”
春去秋来,争论慢慢消失。直到1973年,档案馆工作人员检点文件,无意翻出当年批示原件。批示下角还有一行小字:“以史为镜,留尺幅人情”。看字迹像补描过,究竟是谁加的无人能断。管理员把文件连同密封袋锁入金库编号“67-ZT-002”,自此再无外传。

1995年清明节前夕,李淑贤携骨灰移葬河北易县清西陵。汽车拐过昌平时,她突伸手拍窗,司机猛踩刹车。她望向远处青山低语:“那里有先祖长眠,他想到那儿走走。”工作人员在西陵东南角腾出一隅,立一块小碑,碑文如前,未增一字。
如今青石碑前,青草漫过刻字,游客鲜少驻足。风过松林,只有偶尔能听到看陵老人的絮叨:“当了一辈子风云人物,到头来也就是一抔土。”
嘉正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